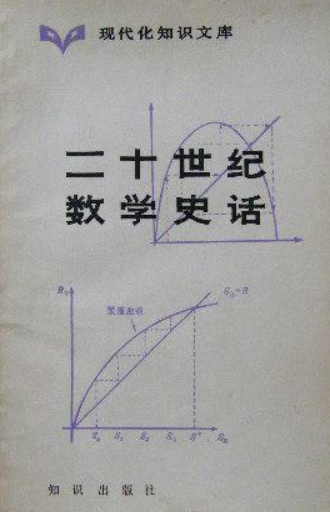
惊闻先生去世的消息,我正在一所小学听课,顿时,大脑一片空白:周围的声音仿佛被屏蔽了起来,眼前的画面也模糊不清了,这些年先生影响我的点点滴滴渐渐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
认识先生,是在大学时代。那时我去图书馆借书,偶然看到《二十世纪数学史话》。这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,由一个个有趣的数学小故事构成:没有高深的理论,也没有抽象的公式;读起来朗朗上口,趣味盎然。我一下子被吸引住了:这简直就是文学中的白描,美术中的写意。数学家竟然有如此好的文采!我一下子心向往之了。据先生介绍,这本书引起陈省身先生的极大关注与高度评价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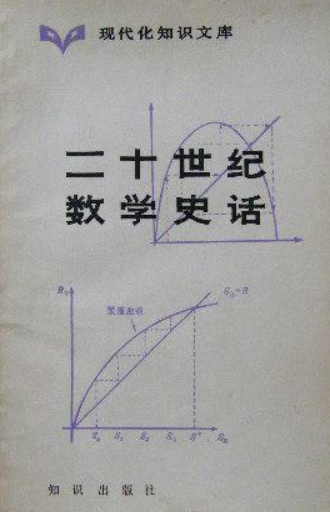
《二十世纪数学史话》
我因此对数学史产生了兴趣,斗胆给先生写了一封信,请他推荐数学史、数学教育方面的书。让我喜出望外的是,先生不久就给我回信了。除了推荐一些书目外,先生还鼓励我好好读一些书,静下心来,不急躁、不浮躁,这样才会有所长进。后来才明白先生的良苦用心:年轻人精力旺盛、血气方刚,但要切忌浮躁,以免走了弯路,虚掷了时光。这是先生经年人生阅历、丰富研究经验的总结。我当时缺少累积,了无察觉。这封信几次搬家,已经丢失了。
与这封信一同丢失的,也包括我对数学史、数学教育研究的热情与兴趣。我也因年轻气盛,徘徊在人生的路口,蹉跎了不少岁月。
2003年7月,我有幸到西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,师从数学教育家宋乃庆教授。先生是西南大学的博导,因此成为了先生的学生,聆听到先生的教诲。
记得编写《数学教育概论》时,先生安排我撰写“数学英才教育”一节。我对此专题少有接触,有畏难情绪。先生鼓励我一番,然后约我到他的房间,谈了他的想法与观点,又回答了我的一些疑问。先生出口成章,侃侃而谈,条分缕析,鞭辟入里,来龙去脉,一气呵成。我只恨自己没有录音设备,如果有,将先生的谈话录下来,整理一下,就是一篇好的文章。我不敢怠慢,回到宿舍,基于先生的谈话,尽快整理成文稿,然后,查阅、补充了一些文献资料,比较圆满地完成了这项任务。请先生署名,他笑笑说,我只是动动嘴,文章是你写的,你有著作权。

2014年3月,先生来西南大学,主持编写“数学教育系列教材”。先生,江师母,宋乃庆教授等与博士生合影
2008年,先生主编“中国数学教育丛书”,将我的博士论文《程序性知识教与学研究》列入其中。我知道自己的研究还有不少问题,也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;我更清楚,这是先生对我的肯定与激励。2015年,先生与我等开始着手《小学数学教材中的大道理》的撰写工作,当然,该书的思想、框架与主要内容大都来自先生。每次讨论,先生总是特别喜欢倾听一线教师的声音与意见,挂在嘴边的话是“任老师,你怎样看这个问题”,“张老师,我这个想法在小学课堂中行得通吗?”在得到一线教师的肯定后,脸上露出孩童般的笑容。当听到不同的意见时,先生总是说,你们来自一线,最有发言权;我出不了门,在家中,只是想想而已;对于这个问题,还是要经历实践的检验,我也要再好好思考一下。该书出版时,先生与出版社一再协商,把所有为该书做过贡献的人写到封面;还一再说,这是对大家工作的肯定,是应该的。我明白,这是先生对年轻人的关心与帮助,也是对年轻人的鼓励与培养。我现在也特别关注年轻人的培养,尤其激励研究生的进步;每次去小学课堂听课,都带着欣赏的眼光,鼓励的语气。我知道,这是先生用行动示范给我的。

2016年8月 先生与《小学数学教材中的大道理》作者合影
2004年9月份,我到澳门人威尼斯官网访学,清晰记得张师母带我跑遍华东师大、联系宿舍的身影;始终难忘向先生请教的每一个问题、与先生交流的每一个细节、听先生教诲的每一个日夜。当时,先生正在思考“中国学习者悖论” ,总结中国数学教育的特色,我们的话题自然由此展开。中国强调“书读百遍,其义自见”、“会背唐诗三百首,不会做诗也会吟”,而国外强调“理解第一,先理解再记忆,不理解不记忆”。是这样的吗?先生问道:有理数乘法,你会算吗?我当然回答“会”。先生又问到:“负负为何得正?”我一时回答不上来。我们讨论了一个晚上,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让中学生明白的方法。先生说,理论上讲,可以在有理数域中证明这个法则,但是,这是后话,是数学形式化的结果。数学形式化后,就变成冰冷的美丽了。数学蓬勃发展的时候,不是这样的。数学教育就要还原数学知识创生时数学家火热的思考,展现这个思考的过程。先生说,数学中这样的知识还多着呢,比如“除以一个数为什么等于乘这个数的倒数”?你可以明天去调查一下大学生,给他们十分钟左右的时间,看看能否说明?我第二天去调查,果真,大部分大学生都会算,但是大都说不清算理。先生又问:小学生学习分数除法的时候,有多少小朋友能够说明算理?教师是用什么方法帮助学生明白算理?他们有没有“高招”?你要到课堂中看看。
正是在先生的一个个追问下,正是在与先生的一次次碰撞中,我渐渐理清了思路,也慢慢明白了方向。也是在先生的指导下,知道了如何把思考引向深入。也是在与先生的交流中,感受到先生对中国数学教育的拳拳之心:他多么希望能够拿出有中国特色的数学教育理论与经验,在世界舞台上与国际同行对话与交流,回答“中国学习者悖论”。先生从那时起,一直致力于回答这个问题,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。我也因此知道,数学教育中,还有如此多的美丽贝壳等我们去捡拾,还有如许多的疑难问题待我们去回答。我因此坚定了研究的实证范式:问题从实践中来,数据从现实中来,结论从数据中来。现在,我特别注重实证研究,为了数据的真实性,几近苛刻、偏执。我知道,这是先生用智慧启迪我的。
也是在上海期间,我问先生,你是怎样认识杨振宁教授的?有人说,你与杨教授是亲家,果真吗?先生说:哪有这样的事情。我女婿是杨先生的博士,加之杨先生曾看过我的《二十世纪数学史话》,因此结识了他。先生告知,当时他正在研究数学史,对杨武之(杨振宁的父亲,我国著名数学家)先生十分感兴趣,有些问题需要杨教授来回答,于是与杨教授建立了联系,于是有了后来的“三访纽约大学石溪分校”,有了《杨振宁文集》的出版。《陈省身传》更是说来话长。本来南开大学安排专人来写陈省身传记,种种原因,这项任务由先生最终完成。陈省身教授说:我一生平平淡淡,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故事,也没有津津乐道的花边新闻,没想到张先生写得这么长,写得这么好。正因为与杨振宁教授、陈省身教授一块做了点事情,先生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先生还告知,他之所以能够与国际数学教育委员会(ICMI)结缘,一是李秉彝教授的推荐,二是实实在在地做了点事情,比如,把国际数学教育的成果推介到我国,把我国数学教育好的做法介绍给国外。先生常常告诫:与人打交道,拉拉家常,说说好话,是可以的;但是这样不能深入,要有深入的交往,还是要共同做点事情。先生主持召开了多年的“数学教育高级研讨班”,没有什么名头,也没有什么封号,也仅仅是做点事情。先生这十几年来殚精竭虑、念念不忘地打造“中国数学教育的特色”,没有什么名誉,也不图什么利益,也仅仅是做点事情。我现在已知天命,也在努力做好一点点事情。我知道:这是先生用实践教诲我的。
2008年,我准备变换工作单位。先生一方面希望我来到南方,一方面又担心我这个北方人不适应南方的环境,一再提醒,要想清楚来干什么,要准备吃点苦、做点事。来到杭州后,也遇到一些波折,也时常感到力不从心。先生叮嘱道:不要急,慢慢来,我五十多岁才开始数学教育研究,只要坚持下来,就能够做点事情。今年中秋节,我去拜见先生,先生的状况让我心痛:思路依然是清晰的,思维依然是活跃的,但是没有了红光满面,也没有了侃侃而谈。我们很快就聊到《小学数学教材中的大道理》。他说:我已经没有精力来做这件事情了,你要牵头,把这件事做下去,把这本书做好。另外,不要局限于这本书,把眼界放得开一些,你们能否成立一个小学数学教材研究中心,好好地研究一下我们的小学数学教材,为数学教育做点事情。先生身体状况如此,说话已经力不从心了,还想着数学教育。我强忍情感,走出院门,泪流满面。
先生走了,放下了他魂牵梦绕的数学教育事业,留下了他探索中国数学教育道路的深深足迹。先生,休息一下吧。

2013年6月,先生八十大寿 先生与我